逝去的二千零三年,看了十一部戏,其中九部是跟着绿野,在倦鸟的组织下观看的。新年伊始,赶上这部《收信快乐》。
还是如往常一样,饿着肚子,慌乱的跑到剧场。领到票后,寒暄一下,径直找座去了。定下神来,开始吃点东西。19:25,判断了一下上座形势,毅然挪到正中第二排。事后证明,这一决定非常明智,因为这是一场好安静的戏,没有场景的变化,甚至演员都基本没有在台上走动,从始至终,面向着正中的观众席。
演出静静的开始了,在有些勉为其难的童稚的模仿声中开始了。两个人就是这么不期然的相遇,四十多年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自此拉开序幕。
不像许多实验话剧,喜欢借助字幕、照片、录像等等手段,来帮助阐述故事,渲染气氛。在这部安静的话剧中,一切都借助书信-文字,借助读信-言语的叙述来展开。然而,芬的妈妈、国的爸爸、他们各自的家人、小孩、甚至芬的那些交往对象……都仿似活生生的展现在舞台上;还有教会学校、服兵役、十几年后台北的见面,四十年后香港、新加坡、夏威夷的秘密约会……那些情景也仿佛都被演绎过。
剧的高潮,芬在聚光灯下大声问天,为何拥有就开始失去?国在昏暗的一旁,无声抽泣。黑场过后,舞台恢复如常。国平静略显苍老的交待了后事尾声,芬的辞世为这充满甜蜜、快乐、辛酸、无奈的通信画上了一个句号。重新打开装信的盒子,仿佛打开一个施了魔法的宝箱,时光倒流,瘦皮猴、爱哭芬仿佛顽皮,仿佛活泼的走过。一个信箱,就珍藏了一生的欢笑眼泪。没有人会怀疑,一切真的发生过,存在过,任它化作泥,散成灰。
曲终人散后,很久不能回过神来。舞台上,好奇的观众聚到那颗温馨的圣诞树(抑或是其它的什么象形)前,问候那些小纸片。而我,脸上残泪未干,心柔软的不能动。是的,柔软,这场戏看得我的心,很柔软,有些轻轻的疼。
其实,他们都很幸福,真得很幸福。毕竟,他们在生命中,找到这样一个人,可以如此推心置腹,可以如此任性娇蛮,可以如此长久的,相互见证彼此的生命。我想我没那么有福气,生命对于我,是许多的片断。在这些片断的生命中,有不同的人来承担收信人的角色,比如天真烂漫的儿童时代,有个女孩和我一起分担过早来临的死亡恐惧;从高三开始,有个男孩始终耐心倾听,不论是高考压力,爱情问题,还是旅游见闻,家庭琐事……甚至还从远在万里外的南太平洋,给我一个春节问候电话(但他只是一味的听,却很少向我说什么)。至于现在,我会依靠一个电话号码,分担、分享生命中的喜怒哀乐。
不过,更多的时候,在这些生命片断中,我找不到收信人。所以才会有日记的习惯。不过这个习惯,也荒疏很久了。
没有收信人,或许是因为没有造化,但更多时候,我想是因为没有坦白直面的勇气,或是习惯了懒散麻木的生活。如果不够坦白、直面,我就无法看到我自己,说不出“爱”字,写不出芬的那些信;如果习惯了懒散麻木的生活,我就看不到流浪的小水滴,感受不到生活中的诗意,写不出国的那些信。
出了剧场,空气是清冷的冬天味道,来的时候,司机师傅说,明天是会下雪的。一路步行,用那些小胡同,小四合院、小饭馆,小酒吧,小便利店的人间烟火,舒缓我微微疼痛的心,让自己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一碗馄饨侯的招牌鲜肉馄饨下肚,我已几近完全恢复,打车上路,听交通台那两个活宝讲无聊笑话和脑筋急转弯,这下彻底回来了。
好吧,那就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吧,收不到信,也要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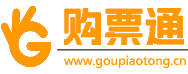




 京公安网备11011202001818号
京公安网备110112020018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