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中国钢琴三杰”之一欧洲巡演结束 11月28日首演国家大剧院

陈萨,世界音乐界眼中和郎朗、李云迪比肩的“新一代中国钢琴三杰”,11月28日,在刚完成一轮欧洲巡演之后,将首次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独奏音乐会。自2001年开始,陈萨在德国汉诺威音乐学院学习,如今她常居汉诺威,也有部分时间待在北京,更多的时间在巡演的路上,她和毕契科夫、斯特拉金、艾杜·迪华特等指挥大师都有过合作,曾与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以色列爱乐等名团携手。在回京前一天,她与记者通了一回越洋电话。学琴生涯 “无公害”的成长
70后、80后的演奏家,已经逐步挑起中国音乐界的大梁。你对于自己和同龄一代的钢琴家的位置,有什么看法?
陈萨:有时候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许多老一代的大师都走了,而还没到20岁的年轻人也有一大批,我们在中间,这意味着什么?就我来说,我还没忘却对前辈仰慕、追随的心情,老一代大师的音乐审美,会一直带领我们走向未来。而我看着很年轻的小孩,确实会有代沟感。许多小孩,学习态度在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有一回我跟一个从美国朱莉亚学院来的十八九岁的孩子聊,他的竞争意识很强。他说自己本来不这样,但在学校里每个人都在攀比。我因此也看到了一个现实。
新京报:你学琴的时候,包括跟但昭义老师,以及在汉诺威求学期间,氛围很不一样?
陈萨:小时候学钢琴是我自己的选择,完全孩子式的,“我喜欢,所以我要”。跟但老师学琴的时候,学习班里的氛围很健康,很良性,很单纯。后来在国外也有很好的环境,安全感是少了一些,但老师会跟你聊很多,而且每周都有一个“班会”,每个学生上去弹一段,是大家都在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过程。我学习的过程比较“无公害”,没有添加化学元素。但当时在学校里也看到有些同学经常考虑的是如何去吸引人,这种意识没有错,但也可能是肤浅的。
新京报:跟两位同代的中国钢琴家相比,你事业的发展似乎慢得多。
陈萨:对我来说,从来没有一夜成名的神话。1996年只能说是奇迹般的事情,是年轻学生一个很好的经历。当时我参赛,主要是从学术上考虑的,之前我参加了1994年的中国国际钢琴比赛,成绩很好,那时接受到了邀请,才参加了英国的比赛。当时是个很大的决定,觉得比赛高不可攀。后来我跟但老师决定去试一试,不是想着要搞合同、找机会,而是想多积累一些曲子,见见世面。
艺术判断 商业化不该主导音乐的取向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古典艺术家担当商业代言?
陈萨:尽管现在的世界非常商业化,但我觉得这个变化不应该主导音乐的取向和实质。搞音乐是很个人化的东西,是要关注现实,但跟现实有一定的距离。缺了商业可能什么都干不了,但商业不应该影响做音乐的过程。目前我还没碰到过什么需要我做出对商业化妥协的情形,妥协了也不见得完全得到自己想得到的。我的音乐世界还比较完整。
新京报:中国现在有上千万学钢琴的孩子,都成为一个奇观了,但未必每个人都喜欢音乐。
陈萨:现在中国琴童经历的,不可能从体制上去改变,他们必须经过这个时期,大家才有沉淀。大家蜂拥着去学钢琴,现在还有点迷茫,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但过一段时间,肯定会冷静下来思考这个问题。我是会有责任感,但我不是超级明星。现在的社会走的是超级明星的道路,只有超级明星才会引起大众的注意,小孩才会去效仿。
新京报:有些音乐家不仅在做音乐,也介入社会事务。你以后会走这条路吗?
陈萨:所有介入社会事务的人有更强的能力,我绝对不属于这一类,但我很感谢他们的贡献,他们给人类带来了财富。我只会做个纯音乐人。如果只能说两个名字,我最仰慕的前辈,一个是已经去世的李赫特尔,另一个是还在世的索科洛夫。两个人的精神能量非常强大。李赫特尔是一个谜,他经历了化简为繁,又化繁为简的过程,到最后出来的东西,方式很简单,但传递的精神境界真的很高,甚至是“非人类”的。
新京报:你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一直是飞机-音乐厅-酒店三点一线的生活形态为主,跟最初的时候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陈萨:跟2001年、2002年刚开始巡演的时候相比几乎一样,但现在更充实,因为以前自己在音乐上的想法和思考没有完全成长起来,有更多机会面对孤独。
音乐状态 灵感是很邪乎的
新京报:有没有过练琴都不想碰的低潮期呢?
陈萨:从来没想过要放弃,但很多时候,女人容易多愁善感,情绪会波动,那时候必须要以强大的逻辑、想想自己的目标,去支撑不稳定的心境。
新京报:失落是因为什么呢?
陈萨:有时候完全没有原因,突然就那样。如果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对生活的哪方面不满,还容易解决些。
新京报:住在德国,可以在森林里释放吧。
陈萨:我家附近就有一大片森林,在自然界里真的很释怀。那时好像跟许多伙伴在一起,很舒适。我就什么也不想了。在森林里走一走,开心的时候会跑起来。我一直梦想在森林里有个房子。没准以后会发生。
新京报:你喜欢安定自然的环境,跟音乐会演奏家的社交生活似乎很矛盾?
陈萨:各种各样的生活,无论是什么计划,如果始终给它留一个位置,以后就会发生。我会结婚的,也会有小孩的,这些肯定会在我的生命中发生。生活形态的转变未必是替换式的,也许只是填充更多的元素在里面。
新京报:“有灵气”是许多乐评和乐迷对你的形容词。你弹琴,会感觉到跟琴发生化学反应吗?
陈萨:灵感是很邪乎的。我弹琴时,这件乐器带我进入了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感觉更靠近音乐的实质。
新京报:能谈一下跟傅聪的交往吗?
陈萨:跟他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你能明显感受到,傅聪身上每个细胞都在告诉你他想说什么,这是一位表达欲望非常强烈的音乐家。不需要他上课一样跟你提要求,他也许边弹边唱,你就会被感动,而得到启发。
新京报:冒着“绝对化”的险,问你对欧洲、美国和中国的观众,有什么不同的印象?
陈萨:美国的观众几乎不管你弹得怎么样,他们都会很欣赏,但这是很好的呀,他们很善于让别人感受到满足感。欧洲观众稍微挑剔些,但当真的觉得好,他们会发出喊叫,站起来鼓掌。国内观众也许是最挑剔的,哈哈。
新京报:在德国朋友多吗?有没有乐迷成了你朋友的?
陈萨:我没有刻意去融入汉诺威的音乐圈。待在德国的时候,经常跟搞音乐的好朋友们,一起吃饭,聊聊音乐。在美国,有一些忠实乐迷,会主动提供他们的车子,把我带到这里那里,不要报酬。在国内,有些乐迷很喜欢音乐,聊得来,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
■ 人物
不同于郎朗和 李云迪的陈萨
1996年,不到17岁的陈萨,作为最小的参赛者,出现在英国利兹钢琴比赛的决赛舞台上,当时为她协奏的是西蒙·拉特执掌下的伯明翰城市交响乐团。小女孩获得了第四名,但英国乐坛已记住了她,把她请进了伦敦的音乐学府。四年后,她又获得了一个第四名———波兰肖邦国际钢琴大赛。这届赛事,另一个中国名字———李云迪横空出世,陈萨的光芒似乎被遮盖了。不过随后在另一项钢琴顶尖赛事———第12届凡·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中,评委之一的约瑟夫·卡里希斯坦评价说:“从没听过如此这般出色的肖邦奏鸣曲”。别的评委们大概所见略同,于是把“水晶大奖”颁给了陈萨。
不过,大赛们似乎没怎么打扰陈萨的宁静。在同门师弟李云迪话题不断、“超级明星”郎朗一张接一张地发表畅销唱片时,被乐评界视为“新一代中国钢琴三杰”之一的陈萨,今年10月才刚发表了首张全球正式发行的录音室唱片———在PentaTone(五音唱片)厂牌下录制的肖邦两首协奏曲。其实早在2003年,陈萨曾在JVC旗下出了一张《肖邦印象》,但据她说,跟唱片公司各方面的机缘都不成熟,“遭遇不顺”。这次录制的依然是肖邦,但是肖邦的“大部头”,大山一样的前辈们———李赫特尔、波利尼等人,早已有了难以挪移的“范本”。陈萨说,不会想着要去超越。她弹琴,不论曲子有名无名,追求的是自己“到底想说什么话”的方式去演绎。陈萨在新唱片中的表达,当即被伦敦“古典调频”电台选为一周焦点唱片,在每天上午播放,并被评为当月“最佳唱片”;而11月的《BBC音乐杂志》刊载了这样一句评价:“她的演奏将音乐造诣与诗意结合得极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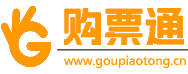




 京公安网备11011202001818号
京公安网备110112020018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