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声日渐边缘化的今天,为自己寻找一个舞台,是年轻相声艺人的唯一出路。近来,流行于北京的“嘻哈包袱铺”由一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组成。虽然演出收入尚不足以维持生活,他们坚持至今的原因只有一个:热爱相声。

北京鼓楼一带,什刹海沿岸的老城区几经修整,幸运地保存了一些老北京的生活气息。2008 年悄然走红的80后相声团体“嘻哈包袱铺”的驻场演出地——广茗阁茶馆,距离鼓楼不到半里地。
悠长响亮的老北京吆喝声响过耳畔;运蜂窝煤的三轮车轱辘,吱吱嘎嘎地碾过马路,鸽哨声盘旋而过。入夜,喜欢听相声的人从四面八方而来,路灯下赶路的身影,透着八十年代赶露天电影般的热乎劲。
老北京茶馆的“嘻哈”范儿
“茶馆从来不是正襟危坐之地,对相声有兴趣的人来这里是为了找乐。
20块钱的门票,谁都看得起。现如今,价钱贵的地方得花60 多块钱。相声成了彰显身份的标签,已经背离了它的土壤。”对于相声的市场和诉求,嘻哈包袱铺的创立人高晓攀看得很清楚。高晓攀生于1985 年,24 岁年纪,言谈举止却透着些与其年龄不相称的世故。
8 岁习艺,15 岁入行,在相声圈里混迹了十年有余,高晓攀时常感叹:“人情世故,我看得差不多了。看不懂的,就到中国传统经典里去学,读‘老庄’、《孙子兵法》、《菜根谭》,这里面已经把许多事理说得很透了。”高晓攀十分信赖中国的传统文化,对相声的痴迷也源自于此。
嘻哈包袱铺演出的广茗阁茶楼有些破旧,从两扇吱吱呀呀的大木门走进去,迎面是直径1.5 米的大鼓。大厅内分上下两层,仿古的桌椅、木窗和光影里的雕花装饰,映射出老茶馆一路走来的漫长时光。
园子里到处张贴着相声演出的海报,一位中年女观众借着昏暗的街灯,细数近期相声演出的时间表。大门东侧20 平方米不到的小屋门旁画满涂鸦和留言,室内墙上挂满八十年代流行的海魂衫、红领巾等老物件供出售。售票室旁的墙报写满最近几周座位的出售情况:“满”、“加座”或“包场”,一目了然。
这间小屋也是嘻哈包袱铺的售票场地,观众不间断地赶来询问本周的票是否售完。负责卖票的包袱铺成员孟然一一作答:两周内的票都卖空了。事实上,与传统相声社团依靠售票网点售票的情况不同,嘻哈包袱铺的售票渠道覆盖了各式各样的在线工具——MSN、QQ、开心网、论坛、豆瓣……不一而足。嘻哈包袱铺一周在广茗阁演出四场:周三周四周五各演一个夜场,周六下午一场。夜场演出晚7点半开始,7点不到观众纷纷落座。二十四张八仙桌,加上大厅两侧的包厢和二楼的座位,约220 个座席。
演出开始前,堂口里放的是北京RAP。看客的吃食也带着明显的时代标记。通常,传统老茶馆的八仙桌上,只有茶水、瓜子、花生和果仁;到了广茗阁听相声,桌上的吃食当中,茶水、可乐、咖啡、“营养快线”、肯德基无所不包。观众大多是35 岁以下的年轻人。2008 年5 月开张以来,一些年轻的观众听了喜欢,就带着父母一起来,慢慢的,观众群不再被年龄限制。
与其他相声场子相比,嘻哈包袱铺的演员休息室是最开放的。演出尚未开始,不论观众、粉丝、演员或记者可以自由出入休息室,与演员自由攀谈。这间有些逼仄的室内墙上,马克笔画满了凌乱的留言、流行歌曲的歌词和涂鸦。屋里的小柜上堆放的则是嘻哈音乐杂志。嘻哈包袱铺给人的印象首先是视觉上的。
据说,到了夏天,总有一只蜥蜴爬在休息室的墙壁上,演员们休息时同蜥蜴逗乐, “看谁先动”便是包袱铺演员们最现成的游戏。“我这个年龄就有一个舞台,让我说上相声,已经很满足了。更何况,我们每天在一起生活真的很快乐。”嘻哈包袱铺的成员王惟很认真地说。王惟的搭档连旭忙着补充除与蜥蜴逗乐之外的游戏,比如演出间隙喜欢一个弹一个“脑绷儿”等等。都是儿时的游戏。
有趣的是,嘻哈包袱铺的观众以女性居多,其中不乏冲着高晓攀的“帅”来的,观众把他描述成“长得很像王力宏的男孩儿”。高晓攀对自己的相貌其实并不以为然,他说:“影视圈不缺我这样的帅哥,但搁在相声圈就显得稀罕了“”,好在,冲着我来的观众,看过一次演出后,就实实在在喜欢相声了。”他腼腆地笑着说。
3 月5 日晚上的演出照例以单口快板开场,接下来一共六个节目, “攒底”通常是高晓攀和搭档尤宪超的“高超组合”。按尤宪超的说法“要确保观众每五分钟大笑两次”,在传统桥段的间隙,不时抖出夹杂着“ ”、“山寨”、“打酱油”等流行词的包袱,台下顿时笑得山崩地裂。
相声是门“熟艺”,这是相声行里人尽皆知的道理,年轻演员惟有依靠不间断的演出,才能历练功力,提高技艺。而在相声日渐边缘化、市场化的今天,年轻一代相声演员已经少有进国家体制内的曲艺团队做职业演员的机会。为自己寻找一个舞台,便是对痴迷相声的年轻一代艺人来说唯一的出路。
迂回前行,只为把相声说下去
白天没有演出,大伙儿也喜欢聚在一起,练活儿或者玩乐。扎堆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相声便在这晃晃悠悠的生活里长了出来。
广茗阁旁的一间酒吧是他们的排练场地。3 月18 日,嘻哈包袱铺的第四部相声剧《山了寨了》即将开演,到酒吧排练的时间拉长了。起先还象征性地点一壶茶,一喝就是一天。后来茶钱也省了。没钱请编剧,高晓攀自己写,春节回家关了三天完成了本子。演员李林有南京艺术学院话剧专业的底子,就干起了导演。每人贡献一点智慧,不停争论与碰撞,在过程中完善。相声艺术是即兴的,也是不停生长的。
20 余名成员大多数辞了职专职做相声,与广茗阁订下三七分成的分配制度,每人每月能拿到一千余元。尽管对付生活还有些紧张,却乐在其中。大抵因为年轻,现实生活的压力还没有实实在在到来,愉快的状态也冲淡了其中的艰辛。
“就这么一天一天往下过,未来会怎样我也不知道。现在说着自己喜欢的相声就很高兴。”排练间隙,演员连旭用一杯开水就把两个卤蛋吃了,算是午餐。那天,碰巧一个开酒吧的朋友来找他玩,他跟朋友说:“你要叫我去你酒吧喝酒,我没钱。要让我去说相声,不给钱也去。”对相声的态度,从只言片语中溢了出来。
他们中的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有着北京男孩特有的乐观劲头。当他们说:“能说上相声,就很开心”、“相声圈是论资排辈的地方,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也能说相声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真的”、“我还年轻,现在不奋斗什么时候奋斗啊?所以没必要说苦”的时候,你会相信,生活原本就应该这么简单、这么纯粹。
相声挣的钱并不够生活,就主持婚礼贴补着过。接到婚礼的活,则先盘算一下当天是否有演出。无论如何,时间和心思都压在嘻哈包袱铺的演出上。
与同龄人单纯的嘻哈做派不同,在高晓攀的处世哲学里多了几分世故。包袱铺火了,他要应付的事也愈多,一度几近失控,但似乎又稳稳地掌控于心。他说: “我跟他们说,以前‘梁山起义’是亲情管理,现在得是科学管理,一切用节目说话”。
高晓攀曾一天接受过21 家媒体的采访, “这些都是必须做的。我必须不停地告诉自己,不断的出发是为了回到原点,相声就是我们的原点。” 对于人情事理的把握力,高晓攀说“这都是饿的,我曾经有过三个馒头吃两天的经历”,语气很豁达。
今年初,高晓攀接到第一部电视剧的活:在台湾电视剧《娘家》中出演男二号。剧组来广茗阁看高晓攀的演出后,直接定了演出合同。5 月,他们将推出关于嘻哈包袱铺成长之路的纪实杂文。高晓攀告诉《外滩画报》, “不久前,姜昆老师对我说: ‘一定要走偶像路线’。”拍剧集、出书也许是偶像化的一种策略。在相声日渐边缘化的今天,爱相声的年轻一代迂回前行,只为能把相声说下去。
8 岁的时候,高晓攀的理想是当奥斯卡影帝,却误打误撞进了老家保定的少年宫,随相声表演艺术家冯宝华学艺,此后慢慢入迷。少年时代,断断续续往返于天津、保定两地拜名师冯春岭学艺。高晓攀一直记得祖师爷带着他去见过马三立的情形。当时,他紧张得直哆嗦,不敢抬头。老爷子眯眼瞅了瞅说,这孩子长得漂亮,在说相声的里面挺少。
如今,马三立先生的风范与气度仍在他心里历历分明,他说: “先生是得大成者。先生有言: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这是高晓攀向往的境界。他用梨园行里的老话“人得自各儿成全自各儿”来励志。在中国戏曲学院学相声时,疯魔到每天守着收音机录下午4 点档和午夜12 点的曲艺节目,然后一板一眼照着抠活儿。别人背老段子《地理图》要用3 天时间,他用了两小时就背清楚了。他心里一直有个愿望“:我一定要火!”
马三立最拿手的贯口《夸住宅》后来成了高晓攀的私爱。当年学这个节目的时候,双手抬平绷直了靠在冯春岭师傅家的墙壁前,死背。冯师傅点拨他:“爷们儿,你这么背可火不了。”于是顿悟:相声须得是说出来的,得像是平时的说话,漫不经心地把人给逗乐喽。技艺随之精进,一天一天更新着自己, “再不会在抖出一个包袱之前,故意提高调门,咯吱人了。”
这段学艺的黄金时段,很快就过去了。大学毕业后,学校张贴公告:“三天后必须离校”,生活忽然变得现实起来:去哪里住?做什么?靠什么挣钱糊口?去798 给画廊做过油漆工,承包过企业的年会晚会,做过婚礼主持……磨难自不必说,但是在少年眼里快乐总归多于烦恼。最开心的是周末下午到陶然亭公园说免费相声, “总有一个舞台,可以说相声。”他说。
2005 年,正是相声回归剧场的萌芽期。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打出“相声回归剧场”的旗号,成立“东城区相声俱乐部”,北京城里的相声社团纷纷开锣,高晓攀参加各式各样的社团演出,技艺长进得极快。后来,自己组建相声团队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小梨园剧场”演出。20 岁就差不多火了,高晓攀说自己有些找不着北,也许是轻狂也许是幼稚,一些老先生们看着不爽,针对他的流言开始在圈内蔓延。“圈子里的水太深了,我看不懂了”,过去了很多年,提到旧事,高晓攀依然一脸迷惑。那时候,喜欢跑后海边一个人哭,想事儿,抑或骑着单车没边没际游荡。北京城里适合演相声的场所,渐渐了然于心,鼓楼大街上的老茶馆广茗阁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活。
成名后怎么走
天天在相声圈里混, “高晓攀”这三个字变成了熟名,2008 年春天,广茗阁茶馆的老板想把周五晚上的演出承包出去,于是找到了他。
一切都那么不确定,当机会来到面前,靠直觉和勇气办事几乎就是一种本能。
“没人敢接周五的活儿,上了一星期班大家都很疲惫,愿意待在家里,谁都知道周五的演出难做,但不接不行,没有自己的舞台,演出就是件不靠谱的事,而我们的活计不能生了。”高晓攀合计了一下,签下了合同。然后,邀约年纪相近的相声同好:王惟和连旭组合是2008 年参加中央电视台组织的相声比赛中结识的;李林和赵臣是在多年的演出中,无数次碰到的;安徽人陈涛是大学毕业后,因为喜欢相声,直接奔北京来的;主持人徐涛则是后来的一次公开招聘考试中发现的。
在日复一日的演出中慢慢练活,每个人都在长进,有了各自的粉丝。演完自己的节目,陈涛喜欢站到观众席旁,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地琢磨:包袱是怎么抖的?如何打开场子?采访的时候,陈涛边看边讲解,一口一句行话“。今天的,这一片场子怎么那么硬呢?”、“尤宪超每天晚上耗活儿,很头痛的” 等等。“耗活儿”指梳理下次演出的节目单。圈子里说的“帅、买、怪、坏”四种表演风格,每晚的演出都要占全,演出形式也要齐全:快板、贯口、单口相声、群口相声一样不能少,抖包袱的方法也不能重样。每天演出完毕,尤宪超都要排好节目表。
第一天的演出,是2008 年5 月16日为汶川大地震的义演。据连旭分析,第一天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观众冲高晓攀而来,一共来了86 人。演出开始时,后台休息室里的气氛无比紧张,台前第一个包袱抖响之后,大伙儿长出一口气,气氛旋即“烧起来了”。“我激动得想挠墙!”连旭的语言富有动作性,这样的语言特质渗透了他和王惟搭档的段子。当天的门票收入和出售嘻哈包袱铺的T 恤的款项,一共2700 元都捐给中华红十字会。
开局堪称完美,但离上路还远,日后嘻哈包袱铺的人一提最“ ”的一次演出,每个人都会翻出“只有两名观众那天”。他们经常调侃“那俩观众去上厕所的时候,我们都琢磨要不要停下来,等他们回来接着演”。
第一个月算完总账,每人分到27元,连旭负责管钱,不知如何分发这27 元工资,想来想去,找来20 多个信封,一个一个封好。于是偷偷观察每个人的表情。“打开后,每个人都是先愣了一下,但马上就笑了。晓攀的笑是我见过的他最意味深长的一次笑。五味杂陈!”
有耐不住性子的人演了几场,不见火,就走了;也有慢慢有点名声后,开始谈条件的人,或者遇到采访赶着抢镜的人都走了。“剩下的就是心特别齐的人,一起练活儿,一起创作,观点不对的时候也扯着脖子争,但谁都心里都不埋根,彼此当兄弟对待。”连旭说。演出就这样不咸不淡地继续着,既没火也没歇火。高晓攀并不着急,大伙儿也不急。开张后的头几个月,媒体来联系采访,都推辞了“。得把活压结实了,才接受采访。”高晓攀这么想。
去年11月,北京某都市报头版刊登了嘻哈包袱铺演出现场的照片,沉寂了半年之后,嘻哈包袱铺有了自己的名声和地盘。演相声能养活自己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能吃上饭是他们最基本的愿望。
但在相声界,好名声未必意味着好收成。作为大众的艺术,20 元定价基本照顾到城市观众的各个收入阶层,轻易不能浮动。而行里的规矩是,前辈艺人没涨价,年轻一代就不能涨,这是约定俗成的。
事实上,虽然火了,但物质方面并没有太大改变。现实和梦想的落差,让人茫然。今年春节后,嘻哈包袱铺的第一次例会有些沉重,高晓攀跟大伙儿说:“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火了之后又怎么样?‘火’带来的感觉很快就过去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走?”这些话也是说给他自己的。
依然是周而复始的演出和刚够维持生计的收入,最初的专注、平静和冲劲却被悄然打破。每天面对的事务几何级数般增长,用来创作的时间和心力被挤得很紧,而在重复观赏的过程中,观众的笑点不断攀升,无论如何,留住观众,是每个爱相声的人和新一代相声演员共同面对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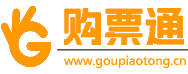




 京公安网备11011202001818号
京公安网备110112020018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