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开放的广场是历史的见证地和艺术制造、产生的场所,那么,封闭的操场除了生长些荒草之外,还能存在些什么?由邹静之先生编剧的《操场》近日在首都剧场举行了首演,解释了这一问题。“操场”也由一个偶尔只出现在青春文学里的词汇,变成了话剧作品中一个象征意义非常强烈的符号。
《操场》一共讲了三个故事,大学教授老迟徘徊于操场,思考和妻子的紧张关系,和童年时的自己对话。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让他内心充满“思索和挣扎”,而拒绝了女学生发出的暧昧邀请,非但没有让他满足于自己的理性,反而坠入更深的绝望中;一个河南民工偶遇在垃圾桶拣食物吃的女大学生,出于同情民工资助了女大学生三年的生活费和学费,但女大学生宁愿用身体“报恩”,也不愿把爱情像一封信那样投到他怀里;一个被告知患癌症三年的人,突然接到医院通知,说他患的不是癌症,而习惯以癌症患者身份生活的他,却不得不在亲人们的异样眼光下,选择了自杀……
三个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都和老迟有关。话剧中的老迟,深受传统道德的约束,有着学者的清高,以及自以为是的生活准则,但心智上的成熟,却解决不了生活中的不如意。他不敢爱,也不敢恨,没有担当,敏感而恐惧,躲避是他唯一能做的事。他在生活这片广场上迷失了自己,于是试图在心灵这片操场上找回自我,但即便在如此之小的天地里,他也发现,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他都是无能为力。
很显然,这又是一部拿当代知识分子开练的话剧作品。韩童生所塑造的老迟形象,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群像的一个缩影。和近两年出现的一些把大学教授描写得十分不堪的长篇小说相比,《操场》中的老迟尽管一样的优柔寡断,但却拥有了可贵的反思精神,虽然这反思精神既没能帮助别人,也没能拯救自己,但老迟在反思的过程中,体会到了痛苦的滋味,在话剧最后,老迟那几声声嘶力竭的高喊,让《操场》有了愤怒的感觉,整部剧也因为这个结尾而得到升华——在操场呆了三天的老迟,也许就此寻找到了自我。
在《操场》中,老迟的“思索和挣扎”并不难理解。整日躲在象牙塔里,两耳不闻身外事,如果不是死人“复活”给他上了生动的一堂人生课,恐怕他会纠缠于自己的拖鞋为什么会唱歌这种琐碎无聊的问题中。
作为龙马社推出的第一部话剧作品,《操场》的最成功之处,在于没有探讨崇高与卑微的区别和界限,而是直面每个人的真实和虚伪。它体现出了创作者的宽容之心,剧中无一可恨之人,皆因他们说出的都是内心的话语。中国的知识分子,既然没有走上广场的勇气,那么何妨不经常到操场上逛逛?那里离课堂只有几步之遥,却有着他们可能永远理解不了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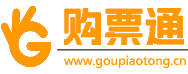




 京公安网备11011202001818号
京公安网备110112020018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