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每个指挥家都是有保质期的”
毕业于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手海汀克,最初供职于荷兰广播爱乐乐团。但心存另一簇火苗的海汀克,在指挥这门课上暗暗使劲,并在32岁时成为乐团史上最年轻的首席指挥,1967年他出任伦敦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直到1979年为止。
1988年,海汀克辞去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职务,以抗议荷兰政府阻碍乐团发展的一项财政决议;同时他增多了与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等乐团的合作频率。多年后,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给海汀克颁发了首个“桂冠指挥”荣誉,30年恩怨,就此算是一朝化解。2002年,海汀克原本担任德累斯顿国立歌剧院的首席指挥,但中途跟歌剧院的管理层发生争执,海汀克遂于2004年辞职走人。
2006年,芝加哥交响乐团出人意料地向老大师亮出了一张四年的音乐总监合约邀请。海汀克愣了一下,委婉回绝:“每个指挥家,包括我自己,都是有保质期的。”
歌剧与交响乐分别是海汀克的左右手。海汀克的艺术造诣得到批评界一致激赏,但他对于组织机构的全面依赖,也常引来争议。
1929年生于荷兰的伯纳德·海汀克,从20世纪上半叶大放异彩的指坛才俊,到今天步入20世纪硕果仅存的指挥大师之列。2月13、14日,海汀克将携芝加哥交响乐团登陆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指挥大师与乐团双双国内首演。适逢今年是“交响乐之父”海顿逝世200年纪念,芝加哥交响乐团将带来海顿《第四十四交响曲》,以及长达80分钟的马勒巨作《第六交响曲》。
1 才子论
指挥也许不太适合年轻人
新京报:你在年轻的时候,一度是指挥界早熟的才子。现在国际乐坛也有不少才华横溢的年轻指挥家,你对新一代有什么期望?你有没有特别欣赏的年轻指挥家?
海汀克:我认为,指挥也许不是太适合年轻人去从事的活儿。当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和国际知名的乐团合作,直到现在,我想起来还会彻夜难眠:因为,我在想,一个毫无人生经历、音乐体验的,乳臭未干的小子,怎么可能胜任这样一个角色?我挺过来了可真是个奇迹。今天的乐坛上,活跃着很多优秀的年轻指挥,但我不想提及任何一个名字。现在的媒体,总是称他们为天才,给予过多的赞誉,这对年轻人很危险。看回我的音乐道路,上世纪60年代时,我和一个著名的乐团合作,那时的媒体不像现在这样亦步亦趋,我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学习和发展,这点很重要。现在的指挥家一旦崭露头角,第二天观众们就能在电视上看到相关报道,这是很危险的;这样的话,年轻人对音乐的态度和选择都在由媒体摆布。另外,每年我都和一批青年学生合作,他们有天赋,都看过卡拉扬、伯恩斯坦这些大师们的视频资料。可他们只是去模仿,而不是要找出自己的风格,这也行不通。现在我正和一位天赋很高的年轻指挥合作,他前途无量,但容我暂时不告诉你他是谁。
新京报:新旧一辈的指挥家之间,交接情况理想吗?
海汀克:关键是看他们的机会了。周围雄心勃勃的指挥有不少,但机会是很重要的因素。我所看到的是,大形势没有以前好,因为没钱了。比如荷兰的乐团,十年前他们不再设助理指挥的职务,借口就是“没钱了”。唉。年轻的指挥需要实战经验!曾几何时,那批人———沃尔特、克伦佩勒、莱纳,他们全都是从一个个中欧的小歌剧院里成长起来的,这样的情景再也看不见了。歌剧院一个接一个关门,歌剧院里任职的人呢,紧抱着自己的饭碗,生怕被后来的人抢去。音乐教育也到了一个青黄不接的关头。
新京报:你开始不是拉小提琴的嘛?
海汀克:没错,但我的理想是当指挥,而且很幸运碰到一个好老师。他是作曲家卡尔·奥尔夫的朋友。每个有天赋的年轻人都得遇上一个乐意扶他/她一把的前辈,看看伯恩斯坦和小泽征尔吧。
2 经济账
伦敦连一个好的 音乐厅都没有
新京报:请问在你看来,音乐的目的是什么?
海汀克:我的老天爷,艺术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没有目的这回事,只有它的存在。我们应该感激它的存在。塞缪尔·约翰逊说:“为什么写作?写作是为了让人类感觉生存没那么难过。”我觉得这话说得极好!
新京报:二十年前,你曾抗议荷兰政府削减提供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经费。乐团经费紧缺,到了今天已经是全球乐坛一个普遍的问题。你对乐团未来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海汀克:我曾经指挥过的伦敦爱乐乐团,就处在两难的困境中。皮埃尔·布列兹说过,在伦敦可以上演任何作品,因为每部作品总有适合演奏的乐师在等着。然而悲剧来自乐团的经营模式。乐团去演奏每场音乐会,其实都在艰难度日。伦敦的音乐生活有多么困难啊,几近残酷。大家的薪水没多高,却时时肩负巨大的压力。乐手们都很优秀而全能,因为这是个优胜劣汰的地方。只可惜伦敦连一个好的音乐厅都没有,却有那么多乐团在抢饭碗。乐团的经理们想得最多的是要怎样去拉赞助,根本没有办法把精力集中到音乐上。而最悲哀的是,这种局面可能会一直下去。
新京报:你曾录制过许多优秀的唱片,涵盖了贝多芬、沃恩·威廉姆斯、肖斯塔科维奇和马勒的作品。你是否曾有这种感觉,无法在当下把握一部作品或者一位作曲家的感觉,必须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才能开始录制这部作品?
海汀克:我一般都选择录制自己熟悉的曲目,它们能带给我家一样的亲切感;我不喜欢去录那些从未在音乐会上演奏过的作品。可是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了:很多曲目都是仅在音乐厅或剧场内上演过两三遍,接着很快就录成唱片了。
新京报:在2004年你曾经声明此后不再执棒歌剧,但去年你在苏黎世和巴黎又指挥了歌剧作品。几年前你也曾提到过不再和英国皇家歌剧院合作了,可前两个月你又愉快的在那里演出了瓦格纳的歌剧《帕斯法尔》。破例有原因吗?
海汀克:我承认,我是自相矛盾了。在这些城市指挥歌剧作品,我都觉得很满意。我不能说我很高兴地指挥了在英国皇家歌剧院的演出,当然我喜欢《帕斯法尔》,可我与皇家歌剧院之间再无瓜葛。
3 作品观
最怕在录音里听到自己的声音
新京报:“音乐作品中,怎样才算得上是杰作”,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
海汀克:自然很有难度。里面有一个技术问题,像皮埃尔·布列兹那样的人可以跟你说清楚,为什么勋伯格是个伟大的作曲家,我就没那么强大了。我说不清楚。伟大的艺术,固然都神秘,比如莫扎特,可能他在生活里只是个普通至极的人,甚至不大好相处。据说他爱说粗俗的玩笑,喜欢赌博,对人很苛刻。可谁在乎呢?谁都无可否认他就是个天才,而且他肯定在某方面存在温暖的人性。瓦格纳很受争议,我的老天,我们如何想像在某些方面待人如此恐怖的人,居然留下那样的杰作?这就是天才的秘密。而人们必须尊重这一切。我们都开心些吧,我高兴的是天才们自行揭晓了谜底,我给不出“怎样才算是杰作”的答案。
新京报:令人兴奋的作品那么多,你怎样选择和决定今天演什么,下周演什么呢?
海汀克:我是欧洲人,对比在美国音乐总监得做出所有的决定,我更适应团队合作的方式。曾经连续25年,我都跟一个艺术委员会紧密合作,共同决定合适的曲目。就算现在,我在芝加哥乐团,也从不会说“我想这样,就这么定了吧”。我会说“我们谈谈?你们整个乐季怎么安排?我怎样参与最合适?”
新京报:你对你所灌录过的唱片都基本满意吗?
海汀克:这问题很难回答。我最怕在录音里听到自己的声音;我也需要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才做得到坐下来坦然地听自己的录音。我从来都做不到在录完一张唱片后马上听,录完了我就放下了。听的时候,我从不对着谱子听,只是随意地让音乐流出来,所以很少会留意技术细节。
新京报:不过,乐迷经常做的事,是在家里听唱片,带着了然于胸的期待来听现场。
海汀克:那样很危险,不可小看的危险。所以我一向很怕别人跟我提:“我有你的这个那个录音,我只爱那版录音。”危险,因为那是“冷冻活动”,你把它放进冷藏柜里,拿出来的时候还是完全一样。这就造成了局限,你会一直带着成见:“那个是最好的。”当你去听现场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自发与自觉,而是一直在拿录音做比较。
4 自我评
我必须认老,但我不服老
新京报:半个世纪的指挥生涯,有什么作品是你一有机会就想演的,或者一直都很难有机会演的?
海汀克:当然有,我一辈子一半时间给了歌剧,一半给了交响曲。而瓦格纳的“特里斯坦”总是避开我。这只是一个例子。当然有人说我可以开声说“我想演这部作品”就行了。其实没那么简单。很多人以为音乐总监就有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我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这回事。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你不想当只手撑天的那一位?
海汀克:(轻笑起来)不不,从那个角度讲的话,我完全不得力。我从未“享受”过权力,从来就不大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从年轻时代我已经发现了这一点。当然,那时我会想要给人留下印象,但很快我就知道那不像我。我宁愿保留自己的骨气,可后来有个很有名望的英国乐评人跟我说:“你当指挥家当得太有理性了”。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我一直喜欢在庞大的机构里工作,因此跟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爱乐有过漫长的化学反应。我喜欢归属于某个机构的感觉,给我一种满足感。
新京报:在你看来,歌剧的观众和交响曲的观众是不同的两批人吗?
海汀克:没错!比如在伦敦,我没演出的时候,也会去看不同的歌剧演出和音乐会,你会发现观众席里基本找不到相同的一批人,跨界的观众几乎没有。这么说有点危险:可我觉得音乐会的听众可能更文明,哈哈。不过,我到四十多才开始指挥歌剧,而我很快就发现,歌剧能在许多层面拓展你的音乐视野,尤其是我在英国的考文特花园和皇家歌剧院的日子。指挥歌剧的优势在于准备的时间很长,你有大把机会去吸收更多更多。
新京报:我知道你在每一次演出前都需要非常充分的准备。
海汀克:无论排练时准备得多么充分,一到音乐会上,永远都是在历险,因为那一刹那,所有乐手,包括我,都会意识到,没有回头路可走。不可能暂停,不可能说话,只能演下去。当我第一次面对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时,我最开始说的话就是:“听好了,我不怎么会说话。”我不属于技术型,不擅于分析,排练时调教得火花四溅,可到了演出时总有点失望。我一来就有一种直觉,同时也保留开放的态度。开放性很关键,我随时把从乐手那里感觉到的诠释出来,再释放出新的东西。我希望用自己的形象、双手以及音乐个性,跟乐团建立起一种只在演出时存在的沟通方式。语言帮不上忙。对着乐手们,你不需要解释什么,只需要获得某种声响,某种平衡。
新京报:当你拒绝芝加哥交响乐团邀你担任音乐总监的四年合同时,你说“每个指挥家都是有保质期的”。执棒五十多年,你如何看待自己未来的音乐道路?
海汀克:我必须认老,但我不服老,不然的话我将一事无成。指挥这门活儿需要大量的体力和脑力参与,我觉得自己依然能有所奉献。指挥的技艺并不在于指间功夫,而独具“姜还是老的辣”的特质。我未来的音乐生涯,要留给后人点评。我享受工作,享受与乐团的音乐家一起合作,这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我和许多有才华的人合作过,我为此觉得荣幸。经历了多年的音乐生涯以来,我仍然热爱音乐,热爱和我一起演绎音乐的人们。
新京报:你觉得当指挥好玩吗?
海汀克:对我来说,指挥是很严肃认真的事。也许因为我常常很严肃,有时还悲观,所以我看不见它好玩的一面。指挥当然带给我无限乐趣,但我从来没有习惯过这种“乐趣”。演出之前的最后关头,无论你已经重复过多少遍,你仍旧会发抖。我从来没有过真正胸有成竹、不需要再看乐谱的信心,心里永远都有一种恐惧:“噢老天,再多点时间就好了!”我们都有野心,所以都需要小心,不要被指挥家的野心夺去理智,小心不要让权力的游戏和政治抢过了风头。我想,只要我还对一部音乐作品心怀敬畏,我还是安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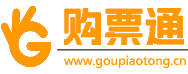




 京公安网备11011202001818号
京公安网备11011202001818号